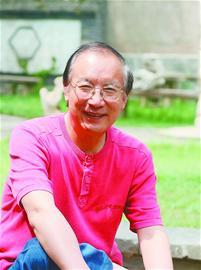




名师简介
沈光伟,1950年出生于山东潍坊,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山东美术家协会理事,山东画院艺委会副主任。
花鸟画作品多次入选由文化部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美展并获奖。作品多次被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首都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国画研究院、山东会堂陈列收藏。
近年来多次应邀赴美国、法国、奥地利、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等地艺术中心和学术机构举办个人画展和讲学。1999年获联合国教科文“世界和平教育者”称号(安南签署)。
众评名师
中国绘画重理念、重才情、重文思的审美理想,天人合一的哲学观,在沈光伟的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或许光伟的画在强调空灵与含蓄美的同时,失去了一些拙厚的强悍,我想这与他的心性有关,画毕竟是画家心灵的写照。以平静的心态去感悟自然,表达心灵的感受,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比起刻意的理性经营和肆意宣泄,要来得真实、来得自然、来得轻松。在《晨露》一画中他也曾题道:“画之灵性往往体现于画之虚处,故日虚灵,从虚处方能洞察画家之修养及悟性,体现画家之画外功,体现大音希声之境界”。可见他走虚灵简约之路的信念是十分坚定的,路还会走得更深更远。
——— 刘大为(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)
曾见光伟落款署“时居乐道院”。乐道,是艺术家自己悟出的艺术心态,也是艺术真诚地从于心的前提。大凡乐于以动植物形象为题材的画家,对大自然必有一颗爱心,必多愁善感于绿肥红瘦、花开花落,有一番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的心肠,甚至于梅妻鹤子般地生出那物我两忘的痴情。藉花鸟以传人之情感体验,表现人的理想品格,寄托人文关怀之精神,是中国花鸟画的美学传统,这也正是花鸟画这一艺术品类常画常新的深刻原因。读光伟的新作无形中使我加深了对乐道者的认识,也坚定了对花鸟画推陈出新的信心。
——— 刘曦林(中国美术馆研究员,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)
沈光伟是中国当代花鸟画坛的“学问型画家”,他以学问为画,当然不是以画来表现自己的渊博学识,而是以画来思考人生的问题。他深知,好的画不是悦人之目,而是契人之心。
——— 朱良志(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名师答问
作为国内花鸟画名家及从教多年的大学教授,沈光伟对中国画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解。近日,记者采访了沈先生,听他畅谈了对中国画教学的独到观点。沈光伟提出,目前中国画教学中的写生课存在偏差,写生不是为了积累素材和培养再现能力,而是要发现美——— 发现美的事物,更重要的是发现美的形式。
济南时报:您从事艺术教育多年,能否谈谈对如今中国画教学的一些感受?
沈光伟:中国画教学在课堂上有两部分内容:一是基础能力培养,二是对画理的理解。基础能力部分,主要是对画面的解读,对经典之作的临摹、学习、研究。了解经典的目的,是培养基本的艺术语言驾驭能力。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有很强的书写性,修养、学识能够从中体现。现在的学生,素描没有问题,但对毛笔的驾驭还需要培养。对画理的理解包括的面非常多。要把对传统的认识纳入画理上来。首先是造型问题:中国画造型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摹写,而是画面的分割,不同的形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;其次是对画面运动的认识,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,是指画面运动的视觉感受——— 是大的起伏还是平缓的运动?在这方面,也是通过临摹,读一些画来加强认识。再次是对节奏的理解,节奏是使一件作品变成艺术品的必然因素,如果没有节奏,肯定不是艺术品。上述三个方面能做到,就能画出很好的画,当然,还不一定是很好的艺术品。艺术品很重要的是一种情感、精神的表达。
济南时报:您自己非常重视写生,数次带学生远赴川西贡嘎山写生。那么,如何看待写生在中国画教学中的作用?
沈光伟:写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?各个艺术院校每年都会组织写生,但写生在高等教育中存在偏差。一般意义上的写生,是到生活中去画一些物象作为创作素材,这远远不是写生的意义。写生的意义并不是培养再现能力,更多的是培养发现美的能力:一是美的事物的发现,二是美的形式的发现和借用。比如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,华不注山用的是荷叶皴。这就是美的形式的发现和借用,恰恰是现代高等教育写生课中缺乏的。这一点课堂上培养不出来。做到这一点,创作就自由了。
济南时报:刚才谈到画理和对传统绘画的学习。您如何看待传统与艺术教育的关系?
沈光伟:对传统应有敬畏之心。没有敬畏,就吸收不到传统的精粹。我给研究生开过选修课,讲谢赫六法。他们本科曾经学到过,但六法到底是什么,都不清楚。有人把六法只当成有美术史意义,这对美术教育是无用的,要变成活的东西才有意义。能够在绘画的不同时期有不同认识,这才是画论。拿六法中的“随类赋彩”来说,你可以注意一下吴冠中的油画,全是西餐的颜色——— 沙拉、菜、面包、咖啡……只是配比不同。而很多人把郭怡孮的画评为“大花布被面”,那是把他看低了。仔细看看,他的颜色像不像瓷器中的金地粉彩转移到了画上?这就是“移花接木”。
很多时候都是认识程度的问题,造成了教学的欠缺。艺术教育还是要有深度,不能因为能力达不到,就不注重这方面的培养。艺术教育对传统的认知应该再加强。传统有底蕴有厚度,不要学得太简单化了。学成死的美术史,就失去了传统的价值。
济南时报链接:http://jnsb1.e23.cn/html/jnsb/20130412/jnsb9819704.html
